
英国青年数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上周出版了新作《传染的规律:为什么扩散,为什么停止》(The Rules of Contagion: Why Things Spread - and Why They St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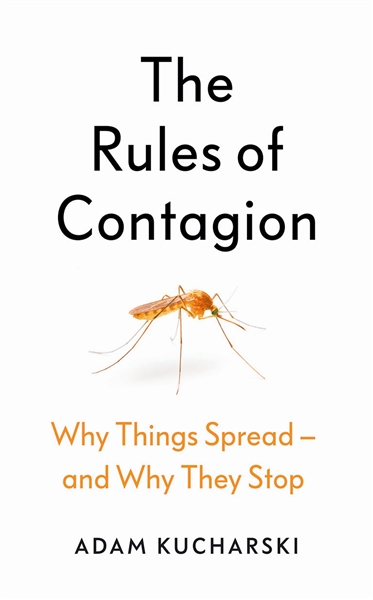
1
《传染的规律》厚三百五十二页,2月13日由韦尔科姆收藏社在英国出版。
这是一本正当其时的著作,不仅因为蔓延中的瘟疫,也由于种种瘟疫般的观念正在世界横行。
好的观念当然也有很多,只是善意的传播似乎常常难以抵挡恶意的扩散。比如,格蕾塔·通贝里的革命理想就远远不及阴谋论的蔓延速度。
三十三岁的库哈尔斯基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相连的世界。观念、思潮,甚至疾病,统统都在更有力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思潮或疾病的传播有着相近的原理。促成它们爆发的,既有随机性,也有隐性规则。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规则,我们需要像数学家一样思考。
在一切传染的核心,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也就是R,传染数。即一个带有某种病毒或某种观念的人可以感染的平均人数。其临界点为1。病毒或观念的R大于1的,将以指数方式传播,少于1的则会逐渐消失。如果R等于1,它将稳定下来,成为地方流行病,或某一特定人群中相对固定的观念。麻疹的R高达20,而埃博拉病毒和流感病毒的R一般在1到2之间。
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医生罗纳德·罗斯(1857-1932)首次发现,疟疾是由一种水生寄生虫引起的,他还认识到,无需扑灭每一个病例,而只需使之难以传播,也就是说,将它的R降到1以下,它就会自行消失。
库哈尔斯基指出,影响R的有四种因素:DOTS,即感染期(Duration)、感染机会(Opportunities)、传染性(Transmission)和人群易感性(Susceptibility)。上述每一项因素的减少,都会使R相应地降低。例如,治愈病患,就能缩减感染期;隔离病患,能降低感染机会;戴安全套或口罩降低了传染性;接种疫苗则降低了人群易感性。
2
但有时你并不想降低R值,反而要尽力推高。比如说,你想利用社交媒体,为某篇文章找到更多的读者,或是光大通贝里的革命思想,或是传播能够救人性命的医疗信息。DOTS的规律仍然适用,尤其是所谓的“病毒式传播”。
库哈尔斯基进而讨论了媒体的作用。暴力、肥胖症和自杀具有传染性,或许尚存争议,但本世纪初芝加哥的枪击事件、近年来伦敦的持刀犯罪事件,确实表现出了与疾病相近的传染规律。但是,观念的有效扩散往往不是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而是通过“扩散性的活动”,借助大众媒体,或是有众多关注者的个人。
“在出版商的办公室,”英国诗人汤姆·奇弗斯在为《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撰写的书评中说,“我猜想他们正在心怀内疚地庆祝这本书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中途上市:很难想象还有比它更适时的出版物了。而尽管写在这种冠状病毒为人所知之前,它在这方面也是一本有用的、有启发的读物。”
在《传染的规律》中,库哈尔斯基还讲了加埃唐·迪加(1953-1984)的故事,此人是加拿大著名的同性恋空中乘务员,一度被认为是艾滋病的“零号病例”,媒体后来称他是“带给我们艾滋病的人”,但他不是。他只是在患病以后,为了帮助调查人员,提供了性伙伴们的名单,没想到乐于助人的美德,让他因为媒体的报道,成了千夫所指的恶棍。如果毫无顾忌地暴露传染病患者的身份,让他们成为社会公敌,背负“超级传染者”、“毒王”、“零号病例”的恶名,那谁还愿意主动帮助卫生机构,去缩减那个至关重要的R呢?
3
库哈尔斯基刚从新加坡回到英国,一度自我隔离,再经测试,确认新冠阴性,才接受了2月16日《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斯蒂芬·布利奇的采访。两人不仅面对面地相见,让布利奇吃惊的是,见面时还发生了新冠时代罕见的赤手相握。库哈尔斯基随后就握手之举作出了当场反思。
“我们得好好想想改变这种行为了。”他说。
作为研究疾病传播的数学家,库哈尔斯基已经全力以赴地工作了两周,与团队一起分析数据,就未来的扩散形势建立模型。“一开始,你详细追踪每个病例,追踪他们所有的联系人,隔离他们,以阻止疾病传播。这很快就会变得非常艰难——如果你突然要处理二十、三十、四十个新病例,这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了。”他说,“我们只希望这种做法在变得不可能之前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窗口期,这样做才行得通:一旦到了某个点,你就根本没有可能来追踪他们所有的人了。”
与普遍的认知相反,库哈尔斯基认为超级传染者的存在是好事。“如果大多数感染只来自少数几个人,就意味着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是不会把它传给别人的。最坏的病毒,是人们走上街就能把它传给周围每个人的病毒,新冠不是那种病毒。”
他的祖父是老师,得过小儿麻痹症,只因为坐轮椅,就被认为智力发育低下。库哈尔斯基因此提醒读者,疾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有社会后果。(中华读书报记者 康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