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子张《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8月18日 1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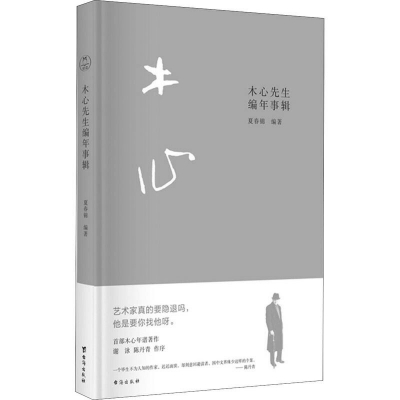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夏春锦著,台海出版社2021年5月第一版,68.00元
木心生命线索中需要填充的空白还有不少,“神秘木心”的形象还有待于进一步寻找更丰富、更可信的资讯去破解。
在我有幸为夏春锦一本读书随笔集撰写“小引”时,就曾经怀着期待预告过一部木心年谱的即将诞生。同是木心的敬慕者,交流多是自然而然的,春锦操持桐乡梧桐阅社时,承他信任,就曾约我去桐乡图书馆与书友们讨论木心先生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问题。《木心先生编年事辑》的最初稿本我大概也是先睹为快者,虽说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并未贡献什么建设性意见,但说到这部年谱著作的编撰过程,我总算最早的读者之一,亲切感自然就更强烈些。
照新批评派的说法,文本一旦形成,便已自足自立,从此可与作者无关,钱锺书先生“鸡蛋与母鸡”的妙喻似乎就脱胎于此派观点。就文本自身作为一个圆满艺术品而言,这当然是说得通的,而且由此及彼,哪一件音乐的、美术的、文字的成熟艺术品不是圆满自足的呢?
可是,这仅仅是就文本谈文本,并不意味着文本跟其“母体”就不再有任何关联,也不意味着那个生产文本的“母体”(作者)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同样不意味着文本隐藏着一切,甚至比“母体”更真实体现“母体”的本质。很多时候,文本可以自足圆满,但却未必可以通过文本去求所写之“真”,认为文本中必包含最真实全面的“母体”即作者,或者把艺术家的作品等同于艺术家的自传,往往只是一种幻觉。也许比较可靠的说法应该是:文本自是文本,作者自是作者,两者血肉相连,却又各自独立。
普通的鸡自然只会生出普通的蛋,若是一只非凡之“蛋”,猜想那鸡也总应该有些不同寻常。如此,蛋既是一件完美的成品,鸡也应该是非凡的母体。钱锺书先生婉谢慕名来访者,要么是冷然于自己的不同一般,要么是性情如此,如其改古人诗句戏言自己“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孤高。
孤高毕竟也还是高,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价值,如珠穆朗玛,如“莎士比亚只有一个”。
除了最孤高的,其他的高都在比较中呈现,如鲁迅,如钱锺书,如木心。
木心名言“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的含义,并非只为推崇艺术而取消艺术家,他是佩服古代那些不留名的艺术家,同时批评当代商业文化、明星文化重“名”轻“艺”甚至为了求名不惜糟践艺术的病态追求。
不然,怎么解释木心如数家珍把尼采、塞尚、纪德时时挂在嘴上又把他们的照片挂在房间里呢?木心也毫不隐瞒他学生时代通过艺术家传记走近艺术的成长历程。
“编年事辑”,从前没有这个说法,也不能算一种正式文体,勉强说,也只可视为年谱的一个别名。而年谱,却又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或者属于传记的初级形式,特点是以编年方式记录传主(谱主)的生平事迹。
不过“编年事辑”既已流行,自然在采用者看来与正式的年谱就存有某些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个体性的,只是因不同作者观念和操作方式的不同而产生,或体现于体例,或体现于行文,却主要并不体现于名称本身。叫年谱还是叫编年事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得比较地好还是比较地不理想。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作为木心研究的年谱类学术成果,目前还只有夏春锦写的这一本,无从比较,或许只能根据体现于该书中作者实际的编撰内容和体例,在年谱撰写的一般要求与该书所达至的程度之间做一些衡量。我并非最合适的评议人,但出于对作者信任的答谢,也只好勉力表达点个人意见。
首先,我理解作者何以避开“年谱”而取“编年事辑”的书名可能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如前所言,在作者的理解里,两个名称的不同也意味着撰写要求甚至层次上的不同,他从自谦的角度取了“事辑”的名义;二是我读是书,的确也注意到由于木心传记资料的相对匮乏,从“年谱”以编年记录谱主生平事迹的要求看,在“已有”和“需有”二者之间仍然存在距离,木心生命线索中需要填充的空白也还有不少,“神秘木心”的形象还有待于进一步寻找更丰富、更可信的资讯去破解。令人称赏的是,在面对某些空白点时,作者并不强作解人,也并未盲目自信,而是清醒意识到此点又坦然向读者交了底。他在后记中诚恳讲出了自己走近木心的不易,更有“只是在个人从事木心生平研究漫漫长途中迈出的一小步”“目前自己掌握的资料实在只是冰山之一角”这样的坦诚。尤其当面对如木心这样虔诚的艺术家时,我以为研究态度的诚恳与谦逊简直就是第一位的要求。而夏春锦这些话和书中那些毫不夸大其词、有一说一的条目,让我对他不能不有所信任,让我直觉到“今后能持续完善”的目标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又不得不说,透过现有条目所征引的木心自述和其他文献资料,可以感觉得到作者斟酌选材的谨严细致。所谓以编年方式记录传主(谱主)生平事迹,并非只有干巴巴的抽象概述,这些概述虽说体现编撰者的个人见解,但“事辑”则最好是丰富的、鲜活的史料,这史料既包括传主(谱主)自述,也该有靠得住的他人的见证或旁证。“靠得住”就需要编撰者的眼光,并非任何材料皆可不加辨析予以收拢的。就这本木心的“编年事辑”,可以说,在目前能够找得到的资讯中,作者摘引的一个一个片段抓住了木心生平的不少“关键词”,如果阅读者肯用心,能够理解编撰者用此不用彼或对某些资讯有而不用的出发点,是可以有所会心、有所收获的。譬如关于老年木心身边那个类似忘年交的男孩,我记得不少人、不少文章都提到,但这本“编年事辑”只采用了一段相关见证人的话给予记录,显然是经过一番比较与斟酌才如此做的,我也觉得相比较而言,这段话对此事的解释比较符合实际。
不管怎么说,作为第一部木心年谱类研究成果,夏著“编年事辑”做到目前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因为它仿佛已有了持续成长的基础——如同一棵树,虽说尚未高大健硕到圆满之境,但已然长成的树干、枝条、叶片给了人们希望:总有一天,它会真正完成自己。
